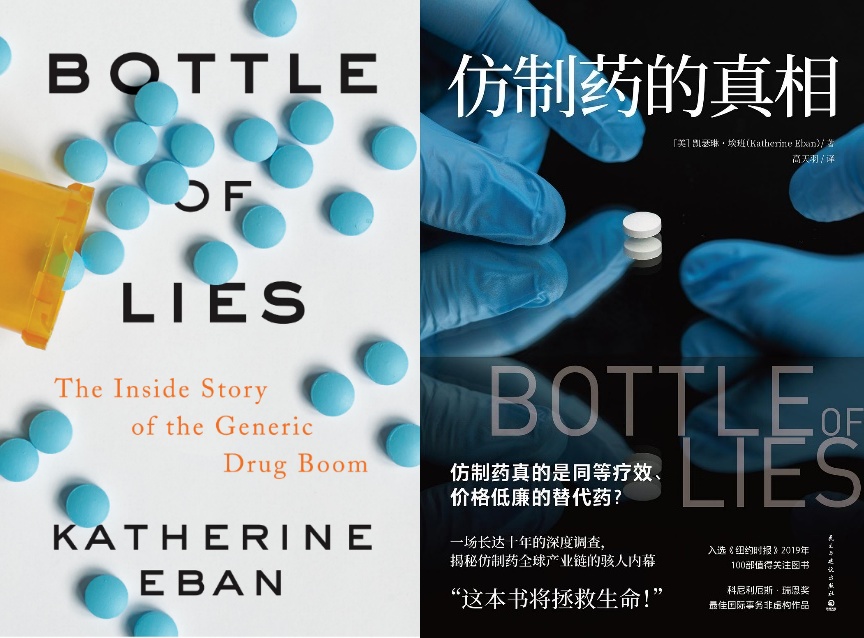
《仿制药的真相》一书颠覆了流行已久的印度仿制药神话,也同时质疑了美国食药监局(FDA)的监管神话。作者逐层揭开真相的过程,亦是逐步降低读者的价值期待底线的过程。尽管全书使用了举报人、执法者以及医学和媒体从业者与罪恶斗争的英雄叙事视角,故事中的好人也都有不太坏的结局,但阅读过程中并无一刻能够感到快慰或轻松。毕竟,对无辜牺牲者而言,正义即便降临,也终归已迟。何况作恶者远未付出应有代价,全球化制药体系的制度困境更远未消除。
该书初版于2019年5月,原题为“谎言药瓶:仿制药繁荣的内幕故事”。中译本2020年10月面市,彼时仿制药质量问题和跨国制药的监管困境并未在中文读者之间引发多少关注。甚至,印度仿制药前后几年间在中文世界的形象主要是正面的,是电影《我不是药神》(2018)中带来生机的低成本仿制格列卫,也是相对易得也相对便宜的仿制版辉瑞特效药Paxlovid(2022-2023)。只在廉价集采药物引发质量忧虑的近期,此书才作为某种域外镜像而受到一些迟来的关注。
读此书可顿悟制药并非慈善事业,药物市场遵循的仍然是最大化逐利的商业逻辑,尽管仿制药厂总是借用“廉价等效药”(p.10)的道德标签,但就事实而言,“高品质低成本的理念只是个神话”(p.278)。药企追求低成本高利润的代价是服药者的健康甚或生命,书中记录了很多服用仿制药导致的悲剧,而恶果与悲剧之所以发生,仿制药企业、监管体系、市场竞争模式、甚至品牌药企业和相关政策的政府决策者都各有其责。
一、恶果:药品质量危机及其牺牲者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生产体系降低生产成本和消费负担,这一做法也适用于制药:依据一项全球协议,印度等国的制药公司能够获准进入“全世界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美国药品市场,美国民众也从而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救命药”,于是有望形成外国药企和美国消费者的“双赢”——前提是,外国药企遵循美国制定的严格的《现行良好生产规范》(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缩写为cGMP)(p.2)。
问题就出在如何确保远隔重洋的外国药企遵循生产规范。生产规范无保障,药物的“廉价”和“等效”就很难兼得。
从结果看,跨国药企显然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出售了不达标药物,以牺牲病人及相关人群的健康和未来为代价获得巨额利润。这些药不怎么要钱,但是要命:一种缓释配方的抗抑郁药专利过期后,一家以色列制药公司推出的仿制药在美国上市,大批患者反映服药后出现头痛、恶心、晕眩、易怒、睡眠问题、焦虑等症状,甚至产生癫痫症状或自杀倾向,无疑,“他们的抑郁症又回来了”。检测表明,仿制药的问题出在有效成分释放过快:作为一种缓释剂型,这种仿制药在服药后前两小时内“向患者体内突然释放的有效成分是品牌药的四倍”,缓释技术的失败既导致了患者报告的不良反应中“服药过量的症状”,如头痛、焦虑等,随之又导致了不良反应中的“戒断症状”,如再度抑郁和自杀倾向。(pp.210-213)
书中两家典型的印度问题药企是兰伯西(Ranbaxy)和雷迪博士实验室(Dr. Reddy’s Laboratories)。一位“一旦知道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情,就会怒不可遏”美国心脏科医生先是发现一些病人使用的兰伯西生产的“低品质的仿制利尿剂”丝毫无效,后又发现心脏移植手术后病人服用的抑制免疫反应、防止器官排异的药物的雷迪博士实验室仿制版无法正常起效,可能导致移植失败。在心脏移植病例中,移植一颗心脏的平均成本“远超100万美元”,同时免疫抑制药物“需要终生服药”,品牌药的每月成本“约需3000美元”;相信仿制药廉价且等效的经济状况不佳的患者难免更换处方,但负责任的医生在“要求我的患者只服用品牌药”的立场上无法让步。这不仅因为相较于心脏移植的这项“投资巨大”且“容不得半点差错”的治疗方案,后期服药不应冒任何风险,还因为那种免疫抑制药物本身即是一种“窄治疗指数药物”(narrow therapeutic index drug),这意味着其“剂量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引起威胁生命的并发症”,因而所需剂量的严格精确性很难被FDA“太过宽松”的生物等效性标准所满足。(pp.188-195)
精密到窄治疗指数的免疫抑制剂,普通到日常广泛使用的抗生素,仿制药企业都有玩忽职守的致命记录。在监管规范相对严格的美国尚且如此,印度本土及非洲等地的惨况更超乎想象:经由“最明目张胆的欺诈和最恶劣的品质疏忽”所生产的药物被销往“监管最薄弱的市场”,包括非洲、东欧、亚洲和南美洲,而“无论那些药物的缺陷多么明显,世界上总有一个市场会接收它们”,以至于“在印度很少看见有药物批次被退回”。在乌干达,一位义务援助的加拿大医生为一名患细菌性脑膜炎的13岁男孩静脉注射广谱抗生素头孢曲松,无效。当地同事令其困惑地建议改用“同一药物的昂贵版本”,治疗开始生效,但已太迟。非洲各地医生都不得不“每一天都要实施药物筛选”,以应对药品稀缺和大量仿制药的不确定性,有时为了“产生疗效”而“把建议剂量变成两倍或三倍”,有时动用医院有限储备的“高端药”(fancy drugs)来治疗那些“在一轮治疗后应该恢复却没有恢复的患者”。所谓“高端药”,是指品牌药或品质较高的仿制药。在卢旺达和加纳,产妇因为抗生素和防止产后大出血的基本药物不合格而大量死亡,医学原本是一门科学,而这里的患者却只好“祈祷自己的药物能够生效”。(pp.270-277)无独有偶,兰伯西员工也曾遭遇自己的幼子服用本公司仿制的一种强力抗生素后仍高烧不退、医生换用品牌抗生素后立即缓解的情形,而暂时的唯一有效选择只能是“再也不给家里人用兰伯西的任何一种药物”。(p.50)
这里所说的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死攸关的影响,典型现象是耐药性。就这一点而言,不达标的仿制药甚至比假药对公众健康构成了更大威胁,原因在于其有效成分不足量,从而无法有效治疗患者,但与此同时不足量的有效成分又为微生物提供了绝佳的自然选择环境,“足以杀死弱小的微生物,并留下那些强大的”。经过这一自然选择而演化出的新一代病原体“甚至能够抵挡那些妥善生产、效力充分的药物”。(pp.279-280)此处关于耐药性的讨论格外值得反思抗生素滥用的国度关注:我们曾在支原体感染流行时广泛讨论抗生素失效问题,有科普文章强调耐药性问题比仿制药问题更值得重视1,但更严重的可能性是,这两个问题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同一问题。
二、困境:盈利动机、竞争模式及监管标准
仿制药厂追求速度、压缩成本和无视生产规范的逐利倾向,加之药品市场称不上良性的竞争模式,及FDA堪称失灵的海外监管体系和复杂不清的利益取向,共同构成了仿制药质量危机的成因。这些因素也使得依靠若干孤勇者才勉强揭露罪责、惩罚恶者的病态现实难以通向实质的改善。
印度和其他海外药厂有充分动机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又不得不假装奉行《现行良好生产规范》,于是,欺骗性检测或编造检测数据就成了基本操作:“它们操纵检测以取得正面结果,隐瞒、篡改数据以掩盖形迹。这些企业在没有必要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生产低成本的药物,然后将这些药物销售到监管严格、价格较高的西方市场,他们宣称自己遵守了所有必要的规章,由此获得巨额利润。”(p.3)
对检测的“操纵”是对严苛标准的激烈嘲讽。原本,FDA由监管产品转而监管生产过程被认为是一次关键转变:对所有生产环节保持记录和检测,坚持“过程验证”,以期“将品质内化于过程之中”,每个步骤的生产数据都必须符合一项首字母缩写为ALCOA的准则——“可追溯”(attributable)、“易辨认”(legible)、“当场记录”(contemporaneously recorded)、“原始版本或原样复制”(original or a true copy)、且“准确”(accurate)(p.40)。这样一来,就达成了良好生产所要求的“完全管控”(p.88)目标。
逐利的仿制药企业的通行做法则可概括为缜密的失控:“操纵了生产过程的几乎每个环节,从而快速制造出漂亮的数据”,以确保盈利。操纵手段往往是高级别管理者授意公司科学家做的,主要包括:(pp.79-95)
1. 严控成本,最大化牟利:为了降低成本,将药物使用的高纯度成分替换成低纯度成分,甚至使用市场上“最便宜的原料”。
2. 盗用原研药,最优化检测结果:为了在粗制滥造的同时确保生成最佳检测结果,直接盗用品牌药的检测结果叠加在自家药物的检测结果,让数据“好得不像是真的”。或者,直接盗取品牌药实物,磨碎后装进自家胶囊,代替自家药物接受检测。
3. 操控受试者数据和样本数据:当真正进行一些检测时,将小型研发批次夸大为规模百倍的展示批次,只对较易控制的小批次欺骗性开展生物等效性和稳定性检测。招募少量患者但生成大量数据,以至于不同患者的数据图形一致得“像是复印出来的”;易控制和欺骗性则体现为,将未通过纯度检测的有效药物成分与检测结果良好的成分混合,直至结果符合要求;而商业规模的批次总是未经检验即出售。
4. 伪造数据和文档:在敷衍的检测仍然数据不好时,修改检测参数并伪造溶解研究。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档都经过修饰,公司的标准生产流程也是捏造。甚至,修饰和捏造也并非生产过程中同时记录,而是事后补缺。为了让新补的记录文档看上去更早,迎检的员工“连夜”将之放进一个潮湿房间加速其做旧。
5. 文档缺失和文档修改权限失控:在审批环节,面向监管不严格的市场时甚至未提供“公司产品的验证方法、稳定性结果及生物等效性报告”。在真实生产中,生产记录“几乎不加管控”,太多工作人员有权修改检测结果。
由此不难想象,这样的药企或许在制造文件和痕迹管理方面花费了比制造药物和生产管理更缜密的心思、更高超的技艺。用作者的话说,兰伯西更擅长“制造借口”(making excuses)而不是“制造药物”(making drugs)。(p.148)
问及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档中有多少数据与公司档案不符,答案是,提交给美国和欧洲的有50%到60%作假,提交给印度本土的则为100%编造。问及为何不能严守“过程验证”和完全管控,答案是,“开展实验的同时记录数据不符合印度文化”。
那么,这里的印度文化指什么?答案一是人脉说了算:监管者“根本不看数据”,要通过印度药品管控总局的审批,“需要的不是真实的数据,而是良好的人脉”。答案二是“不出事就行”,这是制药厂的真实生产标准。
要确保药物既可及又安全有效,实在困难重重。毫无底线的仿制药厂固然是劣药罪恶的元凶,但“廉价等效药”神话的塑造和破灭背后推波助澜的力量还包括原研药企的利益博弈和监管手段的无力或失灵。关于原研药企在药品可及性问题上的角色,直接引用作者一针见血的概括:“患者往往认为,他们服用的仿制药和品牌药完全相同,部分原因是他们想象的是一个简单而友善的过程:在一种药物专利过期之后,品牌药公司就会交出配方,接着仿制药公司就会生产出同样的药物,但成本只有一个零头,因为它不必再在研究或营销上花钱了。”事实却是,仿制药不仅不能完全绕过研发过程,而且一切既关乎科学又关乎法律,过程中始终要应对品牌药公司的专利壁垒。(p.75-76)
关于监管者在药品安全有效问题上的角色,对其质疑似乎并不比对罪恶药企本身的质疑更少:FDA作为“世界上最严格的药物监管机构”(p.49),是怎么让兰伯西这种漏洞百出的仿制药企业不断拿到批文和通过检查的?况且,即便仿制药企业恪守科学和良心,FDA所使用的药物达标标准本身也无法令人毫无顾虑地使用仿制药。
对严苛的ALCOA生产过程监管标准形成显著对照,甚至对之构成另一种激烈嘲讽的,是仿制药“生物等效性”标准的宽松区间:FDA于1992年定义并沿用至今的“生物等效性”标准是一个取值范围,其严格程度“比一般认为的要低得多”(p.208):仿制药的血药浓度不低于品牌药浓度的80%,且不高于它的125%,同时要求检测的置信区间为90%。
对比过程监管的苛刻标准和结果要求的宽松标准,这无异于为一种考试设置严格的考试纪律,甚至具体到文具摆放位置、肢体动作规范、答题时间分布和细碎的考场记录,最终却同意六十分以上均可同等定义为优秀且不公布分数。这显然对药物使用者构成了现实困扰:同样“生物等效”的不同仿制药之间,可有上下浮动45%的差异,以致“如果患者从一种仿制药换到另外一种,可能今天的这种还是最低浓度,明天的那种就变成最高浓度了”(p.208)。而且,生物等效性标准只考虑峰值浓度的比较,未要求缓释剂型的达峰速率,这纵容了前述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的抗抑郁药物上市,FDA工作人员甚至在广播节目中粉饰称有效成分的提前释放是仿制药的“优势”(p.212)。
[待续]
注释:
一篇典型讨论见https://mp.weixin.qq.com/s/3buwcKbtDLrL4sEt-XJvlg,此文题为“美国支原体肺炎激增,但没人担心阿奇霉素的‘质量’”。现在看来,作者的专业性和立场都值得质疑。
作者:朱泙漫
电话:010-58804184
邮箱:tianxing@bnu.edu.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富中通和大厦10层1002

微信公众号天行LAB